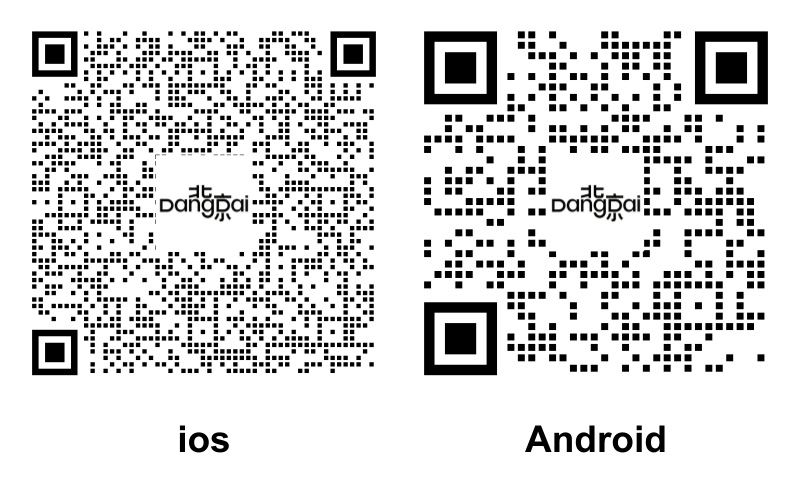「声场」“定量”的装置艺术家和“机缘巧合”的策展人:对话辛云鹏

“辛云鹏:风吹草低”展览现场,2024
图片提供:某某空间
本期「声场」我们对话艺术家辛云鹏,他在诚品画廊策划的展览“讲故事的人”刚刚落幕,在某某空间的个人项目“风吹草低”接续展出。他向我们讲述了他对于装置和雕塑概念的独特理解,他对于艺术家工作方式定量和定性的两种划分,以及他对当下装置和影像创作的多种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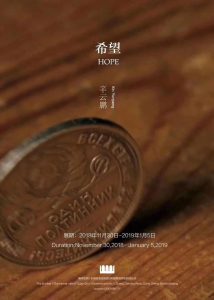

辛云鹏在掩体实验空间的展览“希望”
展览海报和现场,2018

辛云鹏在C5CNM的展览“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展览海报和现场,2020



“辛云鹏:风吹草低”展览现场,2024
图片提供:某某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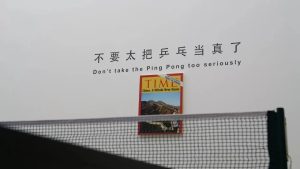

辛云鹏在C5CNM的展览“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现场,2020
XYP:这回展览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有关,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延续为《今天》足球场上的标语“中国第一,世界第二”,两者都是在中文语境里才可以被理解的“口号”。比如“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含义很难被翻译,当然可以直译为“Friendship first, Competition second”,但在竞技运动的语境里其实并不成立。而2022年在卡塔尔世界杯上看到醒目的“中国第一,世界第二”这段广告文字时,在我的意识里,它应该源自于“乒乓外交”。虽然不知道这个广告语的创意者是怎么想的,但从“中文语境”里来看,我觉得肯定有受到“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影响。所以我觉得选择实现这件作品很有趣,可以使两个展览在同一个上下文关系里。



作品《今天》和局部
2024
3000 × 3000 × 250 mm,
灯箱, 5号足球(2022卡塔尔世界杯赛场用球), 5cm仿真草皮, 11人足球赛场专用脚旗旗帜旗杆, 插入式旗杆弹簧腿, 指向性话筒防风套件以及低位三脚架, 打印传单, 线缆, 等⋯⋯,综合媒介
图片提供:某某空间

约瑟夫·博伊斯于1982在卡塞尔文献展现场实施的作品《7000颗橡树》
XYP:这种策略性我理解是将实验性的实践投射到一个经典的概念里,会凸显实践者“走得很远”。在中国当代艺术里也能看到同样的策略。另外,我想强调的是,做装置其实没有必要像对待雕塑一样去处理“经典”的问题,做装置实际上更需要一些灵活性。尤其对于现在的年轻艺术家来说,这种动态的方式更可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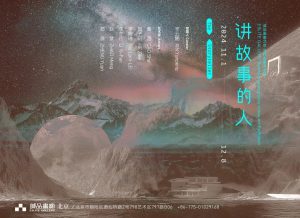


“讲故事的人”展览海报和现场,2024
图片提供:诚品画廊
XYP:展览的标题“讲故事的人”源引自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文本,一战后,新兴出版业的发展导致了一种经验分享的缺失,没有故事和讲故事的行为,都是信息。这个问题放到当下来看也一点不过时。今天艺术界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教育过度”,我曾经和艺术家朋友在私下聊天时说过,现在有些影像作品里的人物对话都不像是“人话”了——其实就是不再去朴素地讲述了,而是不断地告诉观众理论层面或者知识层面的信息。这种影像并不是不好,因为跨学科的东西是值得了解和借鉴的,但是如果很多作品都援引到同一本书,素材和理论来源都差不多,艺术家个体经验在让位给共同的主题和现象,可能就会是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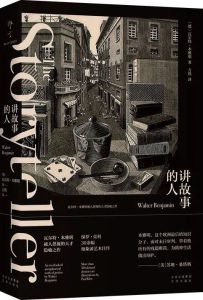
本雅明《讲故事的人》,1936
XYP:今天还有没有艺术家愿意分享个体的经验?所以我选择的艺术家和作品都用某种方法讲述与自身密切的事和经历。回想2008年我刚毕业的时候,感觉遍地都是这样的作品,只要是有叙述内容的影像就都是在分享自己的个人经验。这也跟当时的技术条件有关系,当时还是迷你DV机和数字录影带比较普及的时间,所以影像的风格也大都是记录式的,但能看到很丰富的个体经验和故事。这些在现在当代艺术的环境里变得很稀缺了。


“讲故事的人”展览现场,2024
图片提供:诚品画廊

作品《明天》和局部
2024
圆盘直径1200mm,高度可变,其他依现成品原始尺寸可变。 木, 涂料, 步进电机, 传感器, Arduino控制板, 现成品, 等⋯⋯,综合媒介
图片提供:某某空间


《昨天》和局部
2024
2000x2000x300MM 电机, PVC水池, 高浓缩泡沫粉(视最终效果每日添加500g以内), 时间控制器或遥控感应开关, 等⋯⋯,综合媒介。
图片提供:某某空间
XYP:做装置的话,我自己按计划平时会买一些材料,在罗马湖租的一个库房进行实验。我也自学了作图和编程,不是高手,有时知道逻辑但不会写,现在有了AI也能帮忙了。随着这些工具越来越先进,我有时会反思美院雕塑系的教育是不是落后了,因为到现在雕塑系还是会教你怎样去用铁丝、纱布和石膏这些材料。但这样也有一些好处,就算在最差的环境下你还是能从这些最原始的材料里发现它们的能量。
今天展览里,我们大都将目光集中在屏幕或墙面上来观看,其实艺术家的“领地”在从三维物理空间退让到一个二维的关系里去。我们对空间的思考和批判,变成了一种针对文本或者图像的实践,将身体性让位给了其他“文明”形式,而以前的艺术家恨不得在地上打滚来争取表达的空间。

作品《明天》的局部
2024
圆盘直径1200mm,高度可变,其他依现成品原始尺寸可变。 木, 涂料, 步进电机, 传感器, Arduino控制板, 现成品, 等⋯⋯,综合媒介
图片提供:某某空间